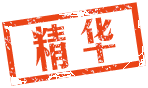作者简介
普拉多斯博士是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高级分析师(senior analyst),也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历史学家,取得了2021年度海军历史作家称号(Naval History Author of the Year 2021)。他的著作包括Storm over Leyte: The Philippine Invas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apanese Navy和Combined Fleet Decod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请访问他的网站johnprados.com了解更多有关他的信息。
1941年6月,期刊统计的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飞机型号、数量和性能参数以及模仿的西方型号。
1941年11月,期刊统计的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航空力量,包括不同种类的飞机和飞行员的数量。
期刊中的文章体现了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关于日本海军装备的情报报告的特点——定量上准确,但在定性上低估(quantitative accuracy but qualitative underestimation)。令人费解的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年和最后几个月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美国海军通过其海军武官办公室(naval attaché office)在东京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情报组织。
ONI的部门
The Desk at ONI
在美国海军,所有外国情报事务均由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ONI)负责。它有一个负责全球各个地区的区域“部”系统(system of regional “desks”)。日本的情报事务在1920年代由D部(Desk D)负责,1931年后由OP-16-B-12(后改为B-11)负责——它们全部属于远东司(Far East Section)。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一直是ONI的主要情报收集目标。
D部在ONI中有一个优势——只需要负责驻日本和中国的武官。中国舰队规模很小。真正的兴趣点仍然是日本海军。和日本有关的附属兴趣——帝国、与泰国的关系、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太平洋上的托管岛屿(Mandated Islands)以及对珍珠港或关岛等地的美国设施的影响——都属于正式由ONI指导的情报需求。
部门的任务也很简单。海军拥有关于外国列强的专著(monographs)。它们是一种类似于国别体百科全书(country-specific encyclopedia)的基础情报产品。其内容包括政府、人口、经济、港口、航运和贸易路线、进出口、关键商品、海军力量——与一场战争相关的所有信息。D部或B-12部可能会要求一名武官特别关注某一方面,但总的来说,华盛顿很少提出正式的情报要求。在海军部,D部的两到三名军官、水兵和文职人员会把将武官报告的信息纳入专著中。该专著于1924年更新,之后定期更新。ONI的1926年年度报告表明专著修订“即将完成”(is almost completed),这表明了这项任务的规模。
1931年,随着中日战争爆发,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尽管远东司仍然没有要求提供后来被纳入关键情报问题的数据,但这场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观察日本军事行动的机会,并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来源——美国海军亚洲舰队(Asiatic Fleet)及其情报官员,还有位于上海等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争夺中国的战争是间歇性的——1931年在满洲,1932年在上海,然后在1937年,从上海和北京蔓延到全国。
战争推动ONI走向新的方向。1935年,ONI开始收集日本海军各类舰艇的活页式水面轮廓图(loose-leaf collections of at-sea surface silhouette views of IJN ship types),也就是著名的ONI 41-42 I。ONI向华盛顿海军造船厂(Washington Navy Yard)、海军研究实验室(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航空局(Bureau of Aeronautics)和建造和维修局(Bureau of Construction and Repair)寻求帮助以处理图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ONI要求加入亚洲舰队的军舰收集日本托管岛屿的照片。当时,来自信号情报(signals intelligence)的数据几乎不会被纳入ONI报告。英国皇家海军和ONI大约在1936年开始交换关于日本的情报,但如果你必须指出一个为美国提供有关日本海军情报的单一来源,那就是驻东京武官。
早期的缓和
Early Détente
爱德华·H·沃森上校(Captain Edward H. Watson,拍照时是中校)。他是间战时期第一位驻东京的美国海军武官。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ONI的D部提供有关日本帝国海军的情报,以纳入其日本专著中。
爱德华·H·沃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担任驻东京武官。在就任之前,他花了一些时间在D部学习掌握当时的专著,并阅读前任的信息。ONI还有一本信息收集手册,为每种情报分配了特殊编号,帮助分析人员将武官报告整合到专著中。
当时正值日本海军的八八舰队计划,此造舰项目将为日本舰队增加八艘超无畏舰和八艘战列巡洋舰,使日本海军成为更加棘手的强敌。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导致日本取消了这一计划,将当时正在建造的战列舰加贺号和战列巡洋舰赤城号改装为航空母舰,并取消了至少五艘其他舰艇。
尽管海军条约在日本遇到了政治阻力,但它导致了美日海军的关系缓和。当时的美国武官莱曼·A·科顿上校(Captain Lyman A. Cotton)被允许参观日本造船厂——这是验证条约得到遵守的理想方式。在1928年至1930年间作为助理武官(assistant attaché)的中校阿瑟·麦科勒姆(Commander Arthur McCollum)参观了日本海军位于吴市、佐世保市和横须贺市的造船厂。1932年,随着日本舆论开始反对两年前签署的《伦敦海军条约》和海军军备限制,武官艾萨克·C·约翰逊上校(Captain Isaac C. Johnson)在寻求参观海军设施时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情报收集业务
The Business of Intel Collection
双方都玩着欺骗游戏,但又都采取了防范措施。其中的重点是拥有精通所在国家语言、了解海军术语和技术、能够翻译和梳理文本含义的语言军官(language officers)。东京语言军官之一的助理武官乔治·考茨中校(Assistant attaché Commander George Courts)接受了吴海军造船厂司令官(commander of the Kure Naval Shipyard)长篇大论的日本海军思想专题报告,以至于他的访问时间被耗尽。相反,据说在1938年左右,武官哈罗德·M·比米斯上校(Captain Harold M. Bemis)被秘密告知,美国海军不愿意让日本军官访问美国造船厂。于是比米斯告诉他的继任者亨利·史密斯-赫顿中校(Commander Henri Smith-Hutton)不要坚持访问日本造船厂,以免日本武官要求回访美国造船厂。
美国武官获得的有关日本海军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日本人自己。除了参观造船厂之外,日本立法机关(Diet,即国会)还就海军造舰问题进行了辩论,其会议记录在官方的《官报》(Tokyo Gazette)上发表。日本军官用最终预算统计(final budget tallies)的副本交换了美国海军拨款法案(U.S. naval appropriation bills)的副本。双方还按照军官资历顺序交换了“海军名单”(Navy Lists)。日本海军的名单还记录了军官当前的职务。
有时,日本海军会接待外国武官参观海军基地或停泊在港口的军舰。武官们参观了扶桑号、山城号、榛名号、长门号和陆奥号战列舰——它们是日本海军建造大和级之前的四级战列舰中的三级的成员。日本海军的国防承包商(defense contractors)还举办了外国武官可以免费参加的公开展览。甚至与支持日本海军的公共组织成员的接触也被用来获取数据。船舶下水、海军节庆祝活动、演讲、官方声明、伊藤正德(Masanori Ito)等海事记者的文章、日本对外国间谍的警告、东京空中演习(air drills)——这些全部被写入报告。
日本的政治事件也影响了美国的想法。1936年2月至3月的政变中,陆军的皇道派暗杀了多名高级官员,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Admiral Kantaro Suzuki)也身负重伤,这对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作用。约瑟夫·C·格鲁大使(Ambassador Joseph C. Grew)在珍珠港袭击前的十年里一直在东京,他赞扬了武官弗雷德·罗杰斯上校(Captain Fred Rogers)和其他人在艰难时期的全面合作。大约18个月后,在日本轰炸帕奈号炮艇(USS Panay, PR-5)之后,新到任的比米斯上校与格鲁坐在他的书房里,听时任海军省次官(Deputy Navy Minister)的山本五十六中将(Vice Admiral Isoroku Yamamoto)以及其他日本陆海军军官讲述他们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弗雷德·罗杰斯于1913年成为上尉(lieutenant)时是美国海军中唯一的日本语言军官,他扩大了家中的餐厅,以便更频繁地招待更多的团体,并收集日本客人的信息和八卦。考茨中校认识并喜欢山本,并多次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其他非正式的间谍机会来自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例如高尔夫球——主实验海军航空站(main experimental naval air station)旁边有一个球场——网球、业余摄影,甚至度假。
充当信使的水手将袋装文件(pouched documents)带给武官,要求他们所乘船的船长将船驶过日本造船厂,以便他们拍照。这也是职业棒球运动员莫·伯格(Moe Berg)所采用的技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参与美国间谍活动。与外交官出示国书一样,到任的武官,甚至是初级军官,通常都会与日本海军同行会面。高级武官会和日本海军大臣(Japanese Navy minister)见面。这些接触是向ONI报告日本海军最高层想法的基础。
与同事分享
Sharing with Colleagues
日本海军军官是宝贵的情报来源。这张照片在日本海军大臣举办的晚宴上拍摄,被拍到的美国和日本军官包括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上将(Admiral Harry Yarnell,前排左四)、未来的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中将(future Combined Fleet commander Vice Admiral Mineichi Koga,前排右二)和武官史密斯-赫顿(第二排左四)。
另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是通过“武官俱乐部”(Attachés Club)。这是一个由各国海军武官组成的圈子,他们定期共进午餐。法国武官在东京任职时间最长,是30年代中期的老前辈。英国武官盖伊·维维安上校(Captain Guy Vivian)的一位助手是工程专家,擅长通过只观察螺旋桨来估算军舰动力设备的功率。
日本在1934年开始设计7.2万吨的大和级战列舰,并于1937年采用了最终设计。与此同时,武官俱乐部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计划。大多数参与者相信日本将打破《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战列舰35000吨排水量的限制。1936年,罗杰斯上校预测日本战列舰的排水量可能为45000至55000吨。两年后,比米斯上校估计日本人正在设计超过条约吨位限制并配备16寸炮的战列舰。他还说,意大利人提供的信息认为排水量会高得多(这是正确的),日本正在建造两艘此类战舰,并计划建造第三艘,可能还有第四艘。一个月后,比米斯在另一份报告中确认了这一观点。令人惊讶的是,第二份报告的日期是在大和级战列舰二号舰武藏号铺设龙骨的五周前(Tokyo attaché report 45-38, “Third Replenishment Program,” 18 February 1938,而武藏号于1938年3月29日铺设龙骨)。
日本人将其在大陆的战争称为“支那事变”(China Incident),这对美国武官来说是一个重大机会。在中国,日本海军首次使用航母空袭、大规模空中轰炸、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海军步兵地面作战和封锁等战术。1937年的上海战役期间,日本海军在城市南部设立了一个机场。亚洲舰队派出一名飞行员J·P·沃克上尉(aviator Lieutenant J. P. Walker)指挥附近的一支美国部队,以便他可以观察日本航母舰载机的行动好几个星期。沃克离开时确信日军效率很高。大多数武官定期访问上海,以了解战争的进度。亨利·“汉克”·史密斯-赫顿(Henri “Hank” Smith-Hutton)曾担任亚洲舰队旗舰上的通信官(communications officer)和舰队情报官(fleet intelligence officer),之后于1939年升任东京武官。他每年在上海待几个月。他喜欢读《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最后的武官
The Final Attaché
间战时期的武官和语言学家(linguists)的宝贵工作在在二战时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在史密斯-赫顿麾下工作的吉尔文·斯洛尼姆中校(Commander Gilven Slonim),后来成为威廉·F·哈尔西上将(Admiral William F. Halsey)的第三舰队参谋部的一名日本情报和语言军官(Japanese intelligence and language officer),他在那里被称为“东京摩西”(Tokyo Mose)。照片中是他(右二)与其他工作人员。
1939年,东京海军武官职位空缺时,史密斯-赫顿虽然是日本语言军官,但只是一名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对于武官这一职位来说军衔太低。格鲁大使之前参观东京大使馆后对他大加赞赏,并要求将他送回去,但ONI却不这么认为。另一位更早的语言军官埃利斯·M·扎卡里亚斯上校(Captain Ellis M. Zacharias)被选中,他曾于1927-28年在大使馆工作,并在那里惹恼了那里的人。听说他即将被任命为武官,格鲁大使和他的顾问尤金·H·杜曼(Eugene H. Dooman)都提出了抗议。海军取消了扎卡里亚斯的任命,然后改变了史密斯-赫顿的命令,把他派往东京,并晋升为中校。
史密斯-赫顿搬进了大使馆边上的一所房子,这个房子是之前最后两名武官居住的,并将他的阅读内容转向了《日本时报和广告商》(Japan Times and Advertiser)。他发现日本人比他早年在东京时更加阴沉和压抑。布料、金属和建筑材料出现短缺。通过整理武官档案,史密斯-赫顿得知比米斯上校对日本人的态度很差,而担任助理海军武官的海军飞行员拉尔夫·奥夫斯蒂则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Ralph Ofstie)提供了有关日本海军航空编制的出色报告。
与此同时,日本警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审问与美国人接触的公民或官员,而武官的信息来源也日益枯竭。日本海军为外国武官举办的最后一次午宴是在1939年底,即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吉田善吾中将(Vice Admiral Zengo Yoshida)就任海军大臣之际。
尽管困难重重,武官办公室还是根据公开资料和美国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收集到的信息编写了大量报告。发送电报的成本是按字数衡量的,因此大多数报告都以袋装形式作为备忘录(pouch as memoranda)。在史密斯-赫顿任职期间,武官发送了有关零式战斗机、“长矛”鱼雷(“Long Lance” torpedo)和升级主炮的最上级重巡洋舰的信息。ONI、舰船局和其他机构的海军专家并不总是愿意接受这些信息。
1939年3月,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到1944年,日本海军将其造船预算增加50%,但岸基设施支出增加了一倍,航空支出增加了四倍。有报告记录了其他武官对日本造舰计划和日本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的看法,包括英国助理武官的估计:正在三菱长崎造船厂2号船台(Mitsubishi Nagasaki way no. 2)建造的船(武藏号)长度必须至少是706英尺(215米)。武官俱乐部的一个重大高估是认为日本正在建造八艘(而不是三艘)战列舰。1940年1月,美国武官的6-40号报告讨论了新造舰艇的16英寸火炮,并补充说,“也尝试过18英寸火炮,但这种火炮从未真正完成”(one 18-inch gun was also attempted but this gun was never actually completed)。1941年11月29日,史密斯-赫顿报告称,泰国海军武官提供的信息显示日本海军最近有一艘45000吨战列舰服役,配备16寸炮,预计在年底前再增加一艘。这些舰艇是大和号(12月16日服役)和武藏号。后者直到1942年8月5日才加入舰队。
最后的日子
The Last Days
随着两国关系恶化,报告仍在继续。1941年11月17日,当日本政府在秘密策划开战时,首相东条英机(Prime Minister Hideki Tojo)在国会发表讲话,要求结束对日本的制裁和停止阻挠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史密斯-赫顿中校坐在旁听席的外交包厢里观察着。东条结束时,他靠向一位同事低声说道:“好吧,无论如何,他没有宣战。”三周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
史密斯-赫顿中校已经预测到了最坏的情况并做好了准备。他购买了日语教科书并将其运往美国用于将来的语言培训。他派语言学家回国,其中包括在战争时期对美国情报至关重要的人员。他们包括鲁弗斯·泰勒上尉(Lieutenant Rufus L. Taylor,未来的海军情报局局长)、阿林·科尔上尉(Lieutenant Allyn Cole)、福雷斯特·贝尔德上尉(Lieutenant Forrest Baird)和中尉吉尔文·斯洛尼姆(Lieutenant (junior grade) Gilven Slonim),以及海军陆战队上尉班克斯顿·T·霍尔科姆(Marine Captain Bankston T. Holcomb)。到12月6日(美国时间12月5日),武官办公室已完成密码和文件的焚烧。
珍珠港袭击当天,史密斯-赫顿起得很早,收听短波广播。他听说马来亚海岸发现了日本军舰。他无法收听旧金山广播,所以他调到了上海。播音员称,总领事建议美国人不要上街。当他到达大使馆时得知了夏威夷袭击事件。格鲁大使派他去日本海军省核实报告,海军大臣的助手证实了此事。
东京的美国人很快就被拘留,并于1942年夏天被遣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登上了一艘意大利客轮,史密斯-赫顿设法偷运了一本日记和一份日本海军中校以上军官的卡片索引(card index of IJN officers above the rank of commander)。他们航行到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克斯(Lourenco Marques, Mozambique)。在那里,他们登上了瑞典邮轮“格里普霍姆”(Swedish liner Gripsholm),该客轮运来了来自北美和南美的日本外交官。1942年7月17日《洛伦索·马克斯卫报》(Lourenco Marques Guardian)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美国和日本的人员交换。记者提到亨利·史密斯-赫顿和简·史密斯-赫顿夫妇(Henri and Jane Smith-Hutton)以及他们八岁的女儿辛西娅(Cynthia)是“我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among the charming people I m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