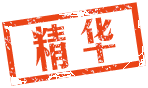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史东 于 2021-11-8 11:08 编辑
第四章 上天入地 海战决不是只在海上作战,其特点是背景、角色和技能极为多样化。首先要注意到,皇家海军是在人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参战的。其直接结果是,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后备人员和志愿者被编成营,作为步兵在陆地上服役。从1914年8月起,这支队伍以“皇家海军师”的名字广为人知,其伤亡占到海军整体损失的很大比例。与此同时,海军也走在现代战争中一个全新维度——动力飞行——的前沿。皇家海军航空服务队在战争开始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航空部队,拥有93架飞机和水上飞机,7艘飞艇,人员接近一千人。到1918年初,当她并入新成立的皇家空军时,已经发展到拥有2949架飞机和水上飞机,约130艘飞艇,55000多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飞机,这种在战争爆发前几年才表现出实际功用的武器,迅速发展出了战术和战略上的用途。
海军大臣丘吉尔“召唤”出飞机和飞艇,为海神增添新的力量。
皇家海军师的征兵海报。该师下辖二旅八营,各营均以海军名将命名。之前提到的寇松子爵是第四代豪伯爵的长子, 他顺理成章地担任了豪营营长,并带队参加加里波利战役。1929年他袭封成为第五代豪伯爵。
最初几个月,皇家海军师还不像后来那么强大。其装备——包括老旧步枪——是急忙筹集起来的,势必存在很多不足。正如伦纳德·塞勒斯所回忆的那样:“我们用的是布尔战争时期那种老式的皮革装具。不用说,它的状态令人震惊……硬得像铁,长满霉斑。”此外,一想到作为海军要上岸打仗,很多人都高兴不起来。二等水兵约翰·本瑟姆回忆道:“准将(旅长)……通知我们,登舰出海的所有希望全部破灭了……这真是一个沉重打击,大家都非常沮丧。我们甚至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模拟葬礼,把一本《海军部船艺手册》沉入泰晤士河底。”训练有时相当敷衍。用伦纳德·塞勒斯的话讲:“(海军)军官对陆军训练一无所知,连长们照着训练手册念出命令是常有的事。”1914年8月下旬,当各营被部署到弗兰德斯地区、在安特卫普周围卷入混乱且快速移动的战斗后,伤亡之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德军的推进还迫使1500名水兵撤退到中立国荷兰,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都被拘留于此。 到1915年初,英国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达达尼尔海峡。这条狭长水道连接着地中海和黑海,关系到英国与盟友俄国的海上交通,当时处于敌对的土耳其控制下。4月,海军部队支援了一次对加里波利半岛(即达达尼尔海峡北岸)的大规模登陆。皇家海军师与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纽芬兰和法国的部队一起参战。登陆第一天(1915年4月25日),该师安森营的亚瑟·提斯代尔中尉因营救被困在克莱德河号运兵船与滩头之间的许多士兵而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肯尼思·爱德华兹在纳尔逊勋爵号前无畏舰上看到了这一幕:“克莱德河号……从烟幕中出现,六艘交通艇拖着满载士兵的划艇驶向滩头。他们遭到小炮、机枪和步枪的迎头痛击,这些武器都作了极为巧妙而有效的防护,士兵们成百地被打倒。”凶猛的首战过后,又是接连数月的血腥战斗,直到1916年1月英军主动撤退为止,仅皇家海军师就死伤7198人。
只过了几个月,该师就被运往马赛,随后开赴西线战场。外科军医杰弗里·斯帕罗回忆起“绵延数里的葡萄园和绿色田野,远处是粉红色山丘……每个车站都有欢呼的人群,他们欢迎我们来到法国,并送上食物和酒。”然而,等在该师前面的是一连串恐怖,从1916年索姆河战役到1917年帕斯尚尔战役,再到1918年英军的最后攻势。斯帕罗还记得,每个人很快就“对死无全尸、血溅战壕的惊悚场面习以为常,但他的脑海中迟早会出现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总有一天,他的鲜血会染红射击台,他残缺不全的躯体会堵住战壕,他的妻子会成为寡妇,他的孩子们会失去父亲。”
1919年,休伯特·特罗特曼退伍了,坦率地讲,他也惊讶于自己能幸存下来。“妹妹在家里迎接我和母亲。我们叽叽喳喳地聊开了。然后母亲去找我亲爱的父亲。她从卧室里冲了出来:‘休伯特,你爸精神崩溃了,他就像根木头一样躺在那里,昏过去了’。他听见我的声音,精神完全被压垮了。皇家海军师伤亡惨重,我觉得他根本没指望我能活着回来。” 克莱德河号在加里波利滩头登陆。
“起锚!”与大海无缘的水兵们在法国战壕里苦中作乐。
无论是在加里波利作战还是受困于法国北部的堑壕,皇家海军师的官兵们注意到空中力量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常见。他们也知道,在头顶上战斗的许多脆弱的飞行器是由海军战友驾驶的。然而,以激烈的独立意识著称的皇家海军航空服务队在专业技能和社交生活上都与传统海军格格不入,同时又沉浸在自己狂热的技术发展进程中。1914年11月的训练手册捕捉到了海航这种敢为人先的意识:“必须牢记的是,目前此事整体处于非常实验性的阶段,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制定硬性的程序规则。” 对于未来的海军飞行员来说,这一时期的训练至少可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可以肯定,当时的教练机完全不像现代飞机这么复杂。它们的最高时速约为50节(93千米/小时),仪表盘上只有罗盘、空速计、高度计和侧滑仪,有时还有温度计。训练也是同样的简单。哈罗德·罗谢尔描述了他的教官所采用的教学方式,飞机起飞后,他在你耳边喊:“现在你把手往前推,你就会下降,明白吗!……再把它(操纵杆)往回拉,你就往上升。”然后他说:“要是你怎么怎么做的话,就会摔断脖子。”然而,这种相对容易的操作却被极度不可靠的装备所抵消。巴特莱特少校1917年3月25日的日记记录了一位飞行员同伴“被人看到……在大约600米高度飞入云层,不久后飞出时已出现大角度侧滑;(机翼)主支柱显然在压力下折断了……机翼被扯掉,机身像炸弹一样尖啸着落地。”发动机故障尤其常见,罗谢尔描述了因此在敦刻尔克附近海面迫降的情形:“飞机入水时我有点晕头转向……我努力振作起来,对自己说‘哈罗德老弟,要是你还不清醒过来、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的话,你就要像陷阱里的老鼠一样淹死了。’”
某舰军官起居室里,军官们正在制作飞机模型,并探讨双翼机与单翼机的优劣势。 海航人员在飞机旁合影。
海航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反飞艇巡逻,轰炸飞艇库、U艇基地和码头,炮兵观测,投放鱼雷,当然还有空中格斗。此外,飞艇和侦察气球也被广泛使用。在各个战场上迅速建立起许多航空站,军舰上经常搭载水上飞机(吊到水面后滑行起飞),还有一些军舰搭建了起飞平台。 在所有的文字记载中,空战的经历最为震撼人心。巴特莱特对1917年6月3日轰炸布鲁日的行动作了以下描述:“现在每一门高射炮都在朝我们开火,我们不停地闪躲,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尽可能地转弯、扭动、俯冲、侧滑,就是摆脱不了,总觉得下一轮齐射就会击中。我们被近失弹的刺鼻烟雾包围着,……DH4(飞机)被炸得体无完肤。”似乎觉得这还不够,一架德国战斗机随后发动进攻,“一颗子弹从我面前一英寸处呼啸而过,将仪表盘上的一个开关打得粉碎。”哈罗德·罗舍尔也记录了被高射炮火射击的经历:“我喘着粗气,缩在座舱里。……我的眼睛一定是像虾米一样从头顶伸出来。”功勋卓著的飞行员阿尔伯特·恩斯通(依据不同资料,其个人战绩为13或15架)用他典型的言简意赅风格,在飞行日志里记录下1917年5月12日在泽布吕赫上空的一次空中格斗:“被德国佬攻击……确定干掉一架,然后机枪卡壳了,被两架敌机追赶,挨了顿痛打。飞机上有36个洞,不得不更换机身中段、机翼等。”
索普威斯“幼犬”式战斗机从巴勒姆号主炮塔上搭建的简易平台起飞。
肖特184型水上飞机在一战英国海航中的地位相当于二战时的“剑鱼”式。加里波利战役期间,1915年8月17日,G. B. 德埃克上尉驾驶一架184型从本米克里号(Ben-my-Chree,马恩语中“我的心上人”之意)水上飞机母舰起飞,因发动机故障迫降至海面,意外发现附近的一艘土耳其大型拖船,便在滑行过程中发射鱼雷将其击沉。因重量减轻,他随后成功起飞并返回母舰。
这样的经历使得海军飞行员们用一种独特的视角看待战争。不过,无论海、陆、空,每个战斗人员都处于广泛复杂的现实影响下,在战斗的恐怖、兴奋与日常的公事、娱乐之间摇摆不定。以巴特莱特为例,1916年11月某天早晨驾机轰炸过奥斯坦德后,他在法国北部作了一次休闲旅行:“午饭后……我在贝尔格漫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古镇,教堂里有漂亮的彩色玻璃窗……(还有)一些美丽如画的老建筑。”杰弗里·斯帕罗这样描述皇家海军师的水兵们:“他们可以冷酷无情地杀死德国佬,……敢于面对九死一生的危险,第二天晚上……还能因为他们的头号宠儿查理·卓别林的滑稽表演而放声大笑。”对所有参战人员而言,在亲如兄弟的朋友和战友当中出现伤亡所带来的震撼性影响必须被弱化和压制。飞行员罗伯特·康普斯顿(个人战绩25架)概括出一种共同的应对机制:“只有不带真情实感地活着,只有转过脸去,拒绝承认友人已死……我们才能坐下来享受一顿丰盛的早餐。”1917年7月28日,阿尔伯特·恩斯通目睹了好友阿诺德·查德威克(个人战绩11架)的最后时刻。事后他在飞行日志中只留下一条就事论事的记录:“看到查德威克的飞机在拉潘恩附近坠海并摔碎。——查德淹死了。”人们尽了最大努力将这些事情隔离在情感世界之外,战争对人类心理的压榨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第五章 水下战争 战前,皇家海军站在许多技术领域——包括水下战争的最前沿。英国第一艘潜艇于1901年下水,随后是一系列新的改进型号,主要用于海岸防御。到一战开始时有60多艘潜艇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包括最新的D级和E级,柴油发动机和经过提升的居住条件使她们能够胜任耗时更长的任务。1914年8月,有168名军官和1250名水兵在潜艇上工作,他们的战时活动几乎没有先例可循。然而,他们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并经常在北海、达达尼尔海峡、亚得里亚海和波罗的海的海军行动中担任先锋。这一过程中,潜艇部队规模急剧扩大,最终击沉了54艘敌方军舰(包括19艘德国U艇)、274艘运输船和补给船。在人员和物质上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损失61艘潜艇,大约1200人阵亡。据计算,在加入潜艇部队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一为这一决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亡率在舰队各兵种中排名第一。
潜艇人员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海军航空兵,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兵种。首先,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志愿加入的。他们的工资明显高于水面舰艇的同级人员,这是加入这种危险生活的诱因之一,但是潜艇人员之间有一种不拘礼节、志同道合的情谊,许多人觉得很有吸引力。与主力舰上近千人、甚至一千两、三百人不同的是,潜艇的人数通常在二十到六十人之间,而且很少有人调进调出。这一点把他们“焊接”成为紧密的战斗单位,也模糊了军衔和阶级的界限,这在大型军舰上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情况因为生活上的局限性而更加突出。潜艇内部每个角落都塞满了机器、管道和阀门,不可能像战列舰那样为精心划分的住宿区和等级分界而留出空间。潜艇上没有厨师,没有服务员提供晚间饮料,也没有陆战队勤务兵擦拭并叠好制服外套。充其量只有几个加热盘和一个小电炉能在情况允许时加热罐头食品。巡逻开始时穿的那些衣服,半个月后返回时已沾满污垢、汗水和油渍。艇长拥有一个铺位,其余艇员就睡在任何能睡的地方。
几名少年兵在C级潜艇的轮机舱(上)和鱼雷舱(下)观摩学习。
即使没有敌人的存在,潜艇上的生活条件也是惊人的艰苦。申请加入潜艇部队的人要接受特别彻底的体检。正如海军部轻描淡写地说明:“入选者必须体质良好,能够承受相当大的身体负担。”因为水蒸气凝结,衣物永远是潮湿的,几天后,艇上的气味被一名军官形容为“最令人作呕的”,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导致恶心、头痛和疲倦,往往使决策能力下降到危险的程度。疲惫让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大多数人每天只能睡上四个小时。 患重病和受重伤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潜艇遇到恶劣天气、潜深波动或搁浅时,脑震荡和骨折是常见的结果。如果海水流入蓄电池,产生的氯气将导致窒息,艇上也不乏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的易燃化学品。潜艇上没有医生,水兵们只能依靠基本的急救技能来治疗受伤的战友。一名上尉讲述了他在一次漫长的任务中被严重烧伤的经历:“我的双脚和双腿……的样子很吓人,长满了像僧帽水母一般巨大的水泡……一着地就疼痛难忍。实际上,我靠抓着管子和横梁来回晃悠才能行动……医疗手册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只提供了几天内的治疗说明。” 水下战争所带来的骇人的心理压力被称为“神经紧张”或“战争震荡症”,也会让人精神崩溃——特别是艇长,他们的每个决定都可能意味着生或死。 E4号艇长厄内斯特·莱尔是英国海军潜艇部队中臭名昭著的补给品小偷,人送外号“飞天大盗”(Arch Thief),据说只有那枚优异服务勋章是他光明正大得来的。其事迹包括:在E4建造时挪用300吨压舱用的铅块,并将“一往无‘铅’”(We need no lead)定为该艇的格言;在某个海军航空站引发火警以转移视线,乘机偷走包括一件毛皮飞行夹克在内的多件物品。后来他卷入了K级潜艇连环碰撞的“五月岛之战”。
重炮潜艇M1号的军官起居室,以潜艇标准来说已是出乎意料的宽敞,拍摄者背后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是12寸炮发射药库。 桌上的银质公鸡是首任艇长马克斯·霍顿(中坐者)的吉祥物。
考虑到人们对这种尚处于萌芽期的技术的巨大索求,机械故障和人为失误进一步催生了事故,有时甚至是灾难,这一点不足为奇。休·斯托克少校记录下1915年澳大利亚AE2号潜艇突然失去俯仰控制、最终导致该艇损失的情景:“她一路下潜、下潜、下潜,60、80、100英尺……几乎是大头朝下。鸡蛋、面包、各种食物、刀叉、盘子从士官食堂里滚滚向前。所有能翻倒的东西都倒了;人们滑倒在地,拼命挣扎着。”事实证明,蒸汽动力的K级大型潜艇特别危险,建成的18艘艇卷入了16起重大事故,3艘在碰撞中损失,1艘失踪,1艘在港口沉没,另有1艘在试航时沉没。后者即K13出事时有80名艇员和平民被困水底,救援人员通过一条装甲管道将一瓶瓶热茶和可可传递给他们,直到一个苏打水瓶不幸卡在管道中才被迫停止。出事57个小时后,艇首浮出水面,但已有32人身亡。 面对这样的挑战,艇员们还能在战争的额外压力下履行职责,这是很了不起的。战争的最初几年,潜艇部队取得了一些突出成就。1914年12月,诺曼·霍尔布鲁克上尉指挥的B11号潜艇突入达达尼尔海峡,击沉土耳其梅苏迪耶号铁甲舰,霍尔布鲁克赢得了有史以来授予潜艇人员的第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与协约国军队在同一战区的陆地上屡屡受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E14号和E11号潜艇在1915年给土耳其航运造成重大损失,她们击沉运兵船,炮击岸上阵地,甚至派人游到岸上炸毁铁路。在此过程中,她们与各种危险作斗争,包括水雷、反潜网和抓钩。著名的一次是,E11号左舷水平舵挂上了一颗水雷,一直拖着它航行两个多小时才得以甩脱。
水面航行中的B11号。
E11号艇员合影,后排左二为艇长马丁·奈史密斯。1912年,英王乔治五世曾经搭乘他指挥的D4号潜艇,体验了10—15分钟的水下旅行,同行的还有阿尔伯特王子(后来的乔治六世)、潜艇部队总监罗杰·凯斯和前首相亚瑟·贝尔福。1915年,奈史密斯指挥E11号在马尔马拉海横行无忌,做下许多胆大包天的勾当,由此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甚至突入了金角湾,据说这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第一次有敌舰出现在金角湾。
在北方,英国潜艇进入波罗的海,扰乱从瑞典到德国的重要的铁矿石运输。正是在那里,1915年10月23日,E8号用鱼雷击沉了德国装甲巡洋舰阿达尔贝特亲王号。艇长弗朗西斯·古德哈特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次猛烈爆炸过后,我向那艘军舰望去,那里只剩下一团巨大的烟云,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条鱼雷的威力确实不小,但它一定是打中了前部弹药库。这幅景象十分壮观,叫人难忘,军舰的残片纷纷溅落在她后方500码的水面上……艇员们非常激动,拍手叫好!……军舰上的人真可怜,糊里糊涂就死了。” 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其他地方,无休止的、时常令人神经紧绷的潜艇巡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随着皇家海军自身损失的增加,潜艇人员的家属(他们大多住在基地里或基地附近)一定遭受了可怕的磨难。当一艘潜艇逾期未归时,女人们会在码头边站成一排,向东张望。她们会在那里一连站上几个小时,外表平静如常,不流一滴眼泪,心中却承受着疑虑和不确定的痛苦。她们不抱希望地希望是一次事故或机械故障耽误了归程,但内心早已明白,亲人所乘的潜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